
【相關報導】Ed Young楊志成的創作世界 —— 從《快樂王子》談起
2001年2月,Ed Young 楊志成,應和英出版社之邀,來台舉行兩場演講。楊志成準備了數百張精采幻燈片(包括數十年最具代表性的圖畫書作品),在演講過程中一一呈現。
第一次聽見《快樂王子》的故事是在我七歲的時候,父親剛從美國留學回來不久,他將這個故事帶回來給我,當時聽了十分感動,所以對這個故事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不過因為年紀漸長,對故事的記憶也逐漸模糊,直到後來選擇以插畫為職業時,有一回偶然問起出版社的編輯,他們是否知道一個關於王子和一隻燕子的故事,結果沒有人記得這個故事,因此我一度以為這個故事是父親自己憑空杜撰的。我父親非常喜歡說故事,孩提時代,當我們傍晚在屋頂乘涼的時候,父親就經常會說故事給我們聽,他只要一說起故事就會天馬行空,口沫橫飛,一直說到我們昏昏欲睡為止,如果故事還沒結束,隔天再繼續。所以後來我也以為「快樂王子」這個故事是他自己瞎編的。
我從一九六二年開始從事插畫方面的工作,大約過了十年以後,也就是在一九七一年時,我到義大利拜訪親戚。一天晚上洗過澡後在親戚家的書房裡閒晃找書看,無意間在書架上看見一本《王爾德童話故事集》,我不曉得王爾德也寫童話,因此就好奇的取下那本書帶回房間閱讀,沒想到書中的第一個故事就是「快樂王子」。我一看就知道這是我小時候聽過,而且一直在尋找的那個故事。那天晚上,我幾乎一
夜無法閤眼,一頁翻過一頁,怎麼也停不下來,一時間,七歲時聽父親說這個故事的情景全都湧現出來。
第二天,我就迫不及待的在畫簿上動筆,將腦海中的影像隨筆畫下來。當時由於不清楚《快樂王子》的故事背景,而自己正好身處義大利,索性就把這個故事放在義大利。於是,我開始在義大利各個城市尋找一處適合成為《快樂王子》故事背景的地方。我的第一張畫就是畫一隻燕子飛進義大利的某一個城市。
接著,我進一步的為這本書找各式各樣的資料和題材,更將自己所畫的作品和對這本書的創作想法帶回美國,和出版社的編輯商談出版事宜,但是那位編輯說,歐洲前不久才剛出版一本《快樂王子》的英文圖畫書,要我最好再等幾年。其實,我已經等了幾十年,再多等個一、兩年也不以為意,可是後來我才知道,原來那個編輯自己不喜歡這個故事,只是嘴巴上不明說,含蓄的要我等一等罷了。
這麼一等就等到一九七八年。那一年我在義大利的一個書展中巧遇一位瑞士出版社的人,他很喜歡我的畫,請我為他做一本書,談話間他不太敢言明那是一本什麼樣的書,只表示如果我不想做也不勉強。後來他告訴我,這本書的書名叫作《快樂王子》。我非常驚訝,不但一口答應,甚至還對他說,我都已經快要畫完了。幾經討論,大家都覺得這個故事的背景不可能在義大利,於是我便將《快樂王子》搬到奧
地利,沒想到瑞士出版社的人說,《快樂王子》可以擺在任何一個國家,唯獨不能放在奧地利,因為瑞士和奧地利是世仇。因此我在心中暗忖,既然這是王爾德是在英國寫的故事,何不就把故事背景設在英國。但後來發現,英國人的氣質情緒和《快樂王子》很不搭襯,因為這是一個很浪漫的故事,而英國人卻相當死板,和故事裡的人物一點都不像。最後,我決定讓《快樂王子》的雕像在法國落腳,所有的建築、服裝都以法國為主。
從七歲第一次聽見《快樂王子》的故事,一直到一九八九年成書問市,這大概是我創作生涯中經營最久的一個作品。當我在義大利的親戚家發現王爾德的童話故事集時,為了保有這個故事,還特別用手抄的方式將整個故事完整的記錄在自己的素描簿上。期間歷經許多波折,也付出許多研究和考證的功夫:例如曾經到歐洲許多博物館找相關資料,查考故事背景,城鎮的樣貌和服裝,也到一些教堂尋找天使的形
像,許多原本無法釐清的疑問,也都在所有草圖完成以後逐漸清澈洞明。
我就是這樣完成了這本書。
問:針對每一個故事,您都會尋找適合的場景和服飾,但是對一般人而言,《快樂王子》是王爾德的作品,直覺就會認為它應該發生在英國。有人認為插畫作品若沒有符合故事真正的時空背景和文化,就會對小孩產生誤導,請問您的看法如何?
答︰可惜王爾德已經過世了,否則我們真應該問問他本人。既然他已經不在人世,我只能單從故事去體會它所在的時空背景。雖然王爾德是英國人,他所寫的不見得一定就是英國的故事,正如同我在美國寫中國的故事一樣,所以不能說美國人寫的就是美國的故事,背景理所當然是美國。每一個故事都有自己的靈魂和背景,我的責任就是從故事中體會應該將它置於何處最恰當。
如果作者還活著,我就會問作者本人,就像《The Girl Who Loved The Wind》的作者還活著,而且是我的好友,因此,當他將故事交給我的時候,我就問他,在你的想法中故事的主角應該是哪一國的女孩呢?他說:「我沒想過,由你決定吧!」我發現這個故事發生在一個靠海的國家,這個國家同時擁有許多花草樹木,並且有許多高大的建築物。我從故事敘述中汲引出各種條件,再以這些條件去尋找適合的場景。我先是將故事背景設定在法國,後來搬到南美,又遷移至許多地方,最後在波斯落腳,因為波斯不但有高大的建築物,也充滿花草樹木,而且最重要的是它就在海邊。後來我打電話給那本書的作者,詢問他是否贊同我將故事背景設定在波斯,作者欣然同意。
因此我猜想,當王爾德在創作《快樂王子》的時候,對故事的時空背景不見得有清楚的概念,作者可以不清楚,但是如果畫圖的人也不清楚,就無法動筆做畫了,因為我們畫出來的場景必須具有足夠的說服力,如果我們無法讓自己信服,又如何取信於人呢?所以每次創作的時候,我都必須耗費許多心力在先前的研究和調查工作,做畫的時間反而無法和其相提並論。然而,這種從尋找到獲得定論的過程對我來說也是一種痛快!
問︰在您完成《快樂王子》以前曾經做出兩個不同的版本,為什麼最後決定以 這個版本問市,您認為它是最好的嗎?為什麼?
答︰這兩個版本各有優劣,最後成書的選擇標準往往和出版社的要求有很大的關係,之所以決定以第二個版本印製,是因為出版社覺得那個版本比較貼近兒童。說故事的方式不僅一種,它會因為目標聽眾或讀者群而產生改變,就好比我今天演講的對象如果換成了兒童,我的講法也會完全不一樣。以我最新的作品《西遊記》為例,如果再讓我重畫,一定也會出現不同的風貌,這和我在創作當下的想法和心情有關。所以不同版本之間無法比較,它們各有特色,但是對我個人而言,我比較偏愛第一個版本的《快樂王子》。
問︰您喜歡以電影的手法來表現故事,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您彷彿是一個導演,那麼,請問您會不會接受自己導演,而由他人完成表演的創作方式?
答︰就每一本書而論我都是導演,但這是一件很麻煩的差事,因為電影導演只要去找演員來演戲,我則是必須自己創造演員,自己設計場景和服裝,再編合成完整的故事,這些都是很瑣碎的事,所以我比較喜歡做好導演的工作,其他的工作可以請人代勞。
問︰請問您是如何成為一名插畫家的?
答︰你相信命運嗎?我很相信。當我開始修習藝術的時候,完全沒想到自己竟然會一頭栽進童書的領域。我最早學的是建築,後來進入廣告公司,參與一項美國國防部徵兵廣告的設計和繪圖工作,那張廣告出來後,為國防部徵募到許多自願軍。不過沒多久,廣告公司因故結束,我也跟著失業,必須另謀出路,我當時對失業不以為意,反正我原本就對廣告工作沒什麼興趣。在找工作的那段時間,我陸陸續續畫
了許多和動物有關的插畫作品,結果有人告訴我,童書裡有許多和動物有關的主題,建議我去童書出版社找差事。
我做的第一本圖畫書是《The Mean Mouse and Other Mean Stories》,是一本將動物擬人化的故事書,書裡的動物總是推來打去,我覺得這對動物好像不太尊重,於是回絕了那本書。但是出版社的編輯不死心,要我把書再帶回去看一看,我和當時也學藝術的室友商量後決定放手一試,沒想到書一出版就得獎,也因此和一位插畫經紀人簽約,然後就這麼一路做到現在。
問:請問您如何安排一天中工作與生活的時間?
答︰我每天工作的時間不一定,腸枯思竭時獃坐在桌前也不是辦法,但是當靈感來的時候,想擋也擋不住。有些畫家會為自己設定工作時間,就像是開關一樣,一打開就工作,關掉就收工,可是我沒有辦法這麼做。
問︰現實生活中有許多挫折和困境,請問您如何在如此不美好的生活中依然能夠創作出美好的書?
答︰每個人有消氣和宣洩情緒的方法,或是看書、看電影,或是從事一些休閒娛樂。雖然生活中難免有令人不順心的事,但總得想辦法挽回自己,我就是透過繪畫挽回自己。若是能夠專注於自己喜歡的事,便可以從中獲得許多樂趣,因為當你廢寢忘食的做一件事時,這往往就是你最喜歡的一件事,一件能夠令你感到欣慰的事。
問︰您非常會講故事,我們也希望父母多為自己的孩子說故事。是不是你的父親也常常講故事給你聽,這對你的創作有過影響嗎?
答:我父親很喜歡說故事,我也喜歡講故事,只是方式不同罷了。我小時候很害羞,所以綽號叫「啞巴」。我故事聽得多,看得也不少。做童書用不著出面講話,因為做藝術的人比較內向,如果要我講話,我就沒輒了。譬如,如果你問我哪一本書是在什麼時候做的,我都不記得了,還得打電話問黃瑞怡(研究人員)。黃瑞怡專門研究我的事情,所以我常打電話問她,我是怎樣的一個人。
問:您有兩個可愛的女兒,請問這兩個女兒對您的創作有什麼影響或啟發?
答︰其實,我不常唸自己的書給她們聽,因為她們還小,理解能力仍有所不及。在我的作品當中,《七隻瞎老鼠》是她們最喜歡的一本,至於其他的作品可能必須等她們年紀稍大以後才能瞭解其中的意涵。畫圖是我的工作,她們在我工作的時候不准進畫室,然而當我和她們一起玩的時候,她們就變成了真正藝術家。或許是因為父母的影響,或是成長環境中的耳濡目染,她也常常會動手創作自己的書,自己寫
故事,自己畫畫,這是很自然的事。我尊重小孩個別的發展,將來她們若想從事這方面的工作,我會助她們一臂之力,但絕不勉強。
問︰在您的創作過程中,對於創作圖畫書這件事,對您影響最深的圖畫書作家或畫家是哪一位?
答︰我的國畫老師對我有相當大的影響,他常常為我指點迷津,幫助我參透那些自己無法明瞭或看不清的事理。有一回我們相約去散步,他便要我留意樹梢上竄冒出來的綠芽,看看樹枝上的「氣」。當時我不明白他話中的意思,也看不見他所謂的「氣」。於是他要我再仔細看,當我靜下來潛心端看的時候,彷彿真的體會到他話中的意涵。造成一株樹生成的因素很多,包括樹的成長方式、枝葉的伸展、風、樹
根、甚至樹旁的石頭和人類,而樹的心靈都是由這些「天地人」的因素造就出來的。
我在藝術學院裡從未聽聞這些事,因此覺得中國人對自然和事物的觀點特別深奧。根據我國畫老師的說法,我必須將自己化身為一株樹,才能領略和體驗樹的成長,因為每一個生命都有一段屬於他自己的故事。
問:您個人比較欣賞哪些畫家的作品?
答︰很多,一時間也想不起來。我每次去看畫展的時候都很有收穫。我們常常會不自覺的受到環境的影響和支配,有時候從我筆端產生的東西,自己也不知道是從哪裡來的,所以我認為環境是很重要的老師。有時刻意想學反而一無所獲,但是如果隨時都能夠保有一個開放的心胸,可能就會學到比較多東西。
問︰您的創作大多由心靈而生,請問宗教是否對您的創作產生影響?
每個宗教都有不同的哲理和意境,呈現出來的風格也不同,您在宗教哲理上比較認同哪一個學派?
答︰很難說。就像我在美國說英文,我的口音時常令人難以辨認我的出身之處,其中夾雜著西方口音,東方口音,也有美國南方的口音,但是當我在說話的時候自己完全察覺不出來。因此,若要明確的指出我受到哪一個宗教和哲理的影響較深,實在難以言明。例如,當你在看一個人的時候,往往無法清楚明辨他的鼻子、眼睛和耳朵到底是像他的父親或母親,因為我們看一個人是看他的整體,你會覺得他的五
官有點像他的父母,但要細究時卻又說不出所以然來,無法確定他的五官是從哪一方遺傳得來。如果你真實的看待自己,就不必理會這些影響從何處而來,若是我要追究自己的每一個筆畫是從哪裡學來的,那我也不堪稱為畫家了。一個人在說話的時候往往不清楚自己的表意方式從何習得,同樣的,當一位畫家心懷其意時,這個意念也會隨著畫筆自然流露。
問:您學了三年建築,對您的插畫工作有什麼影響?
答︰我對建築很感興趣,而建築的背景也讓我的畫很有空間感。我剛到紐約的時候,覺得那裡全是房子,而且建築相當古老。紐約人對自己的建築往往視而不見,因為在紐約街上行走時會仰起頭看建築物的絕非當地人。紐約的建築很高大,紐約人通常都是行色匆匆的在街上履步行進,只有那些觀光客會好奇的仰起頭看建築物。其實,只要仰起頭看紐約的建築,就會有許多精彩的發現。我到紐約以後,就開始不停的畫那裡的房子,尤其是比較古老的建築物,因為紐約的建築物拆得很快,常常我在前一天才剛畫好一棟建築物,第二天就發現它已經被貼上拆除公告了。我覺得非常可惜,所以就拼命的畫。那一陣子我的確畫了很多建築物,那些畫大多是自己收藏。
就空間的概念而言,我們的國畫中雖然鮮少出現建築物,卻有很美的空間意境,正如同我今天早晨所看見的薄霧繚繞的山巒。國畫中有許多空間概念,而且通常只要簡單幾筆就能構成,這就是我覺得國畫比西畫強的地方,因為國畫幾筆就能勾勒出景物的樣貌,其精簡意涵也令人折服,因為「少畫比多畫強」,就像作家們寫作一樣,一個意涵若是能夠用一句話表達完整,何必贅言十句呢?
因此,我覺得自己在美國修習的藝術仍顯不足。一九七六年我回台灣參觀國畫老師的畫展,有一天去他的畫室看他,當時他正在做畫,但我以為他在洗筆,因為他用沾了墨水的筆在紙上擦拭。之後我又看見他在上面添了簡單幾筆,我才知道他是在做畫,而那幾筆真可謂「神來之筆」。
西畫多以臨摹為主,可是國畫大多是從腦中的思維直接產生出來,每一筆都非常正確,所以我後來才逐漸明白,原來自己過去在西方世界所學的藝術不值得一提,因為我做畫的時候仍然必須仰賴雙眼所見的事物。但自從和老師學習國畫以後,我的畫作變成直接由腦中的思維而生,先用眼睛看,將影像或圖案置於腦中,然後在憑自己的想法表現出來,不是注視著物件或照片臨摹,這樣的臨摹畫作大多是死的,
沒有生氣。
問:您在《七隻瞎老鼠》這本書中很大膽的以黑色為底色,黑色對小孩來說並不討好,但經由您的詮釋卻讓小孩非常喜歡。請問您日後是否還有計畫將中國的寓言故事搬上西方圖畫書的世界?另外,您對中國文字很感興趣,甚至將部首和文字本身入畫,或是以圖畫來表現,請問您通常如何處理這方面的主題?
答:《七隻瞎老鼠》(1992)是用剪紙的方式表現,其中那隻小老鼠特別難剪,所以我就先剪出最小的那隻老鼠,再按比例剪出其他的老鼠,每隻老鼠都必須一氣呵成,不能有任何閃失,所以當所有的插畫完成時,便留下了一堆被我剪壞的老鼠尾巴。
《七隻瞎老鼠》在美國問市以後其實受到不少批評,不是因為表現手法,而是由顏色所衍生的種族問題。在美國黑人和白人之間仍存在著相當的對立性,因此許多人批評我,問什麼後來發現真相的是那隻「白老鼠」?其實在創作時我並沒有在種族意題上著墨的意圖,而是從光線的角度切入思考,因為陽光表面上看起來雖然是白色,事實上卻是由許多顏色構成(七色構成一色─正如七隻瞎老鼠的顏色),所以,
如果想要將這些顏色襯托出來就只能用黑色了。我在藝術學院唸書時,有人告訴我,童書千萬不能以黑色作為底色,但是為什麼不行呢?我偏要挑戰一下,待作品完成以後也證明,沒有什麼不可以。我常常到小學或幼稚園看小朋友做畫,他們在做畫時不會有任何禁忌,因為畫圖是沒有什麼規矩的。
我曾經在《Voices of the Heart》(1997) 這本書中以插畫的方式介紹中國文字的美感,將中國文字圖像化。在學校裡和小朋友們講解時,他們都十分感興趣,覺得中國文字非常有意思。例如「好」這個字,就是由「女」和「子」結合而成。我另外還將一系列和自然有關的中國文字轉化為圖像,出版社預備將這本書定名為「天下」。我以這種方示表現中國文字,是要讓讀者可以清楚的明白中國人造字的由來和中國字的寫法,例如「麻」裡面有兩個木,感覺纖維很多,而一粒米落在有水的碗裡就變成了「酒」。
我認為繁體字很貼近畫,西方人比較容易接受。以中國字入畫是我的喜好之一,我的國畫老師經常告訴我古人造字的用意,而中國的哲學往往就在字裡。我時常端看著中國文字,一邊思忖其中的意含,一邊閱讀中國哲學。
問:一本書裡有彩色頁和黑白頁,你如何處理?
答:我會以黑白畫為主。這種情況第一次是出現在《田螺女》,那本書的作者是我的朋友,他到我居住的小鎮上講這個故事給我聽,要我為它做插畫。他說這個故事的時候,我在腦子裡看到許多顏色,不過,我同時感受到相當的困難度,因為那個田螺是白色的,它會反光,而田螺的內層有彩虹般的色彩,每動輒變。我覺得,如果把那種色彩感固定下來,反而令我感到不安。等他說完故事後,我說,我可以幫
你做這本書,可是我想用黑白來表現這個故事。他說,不,我認為應該是彩色的,不是黑白。經過一番討價還價後,我說,我先用黑白畫畫看,如果你不滿意,再用彩色的,可以嗎?結果,當我將成品給他看的時候,他卻非常滿意。因為在國畫裡,黑白顏色運用得好,它表現得比彩色還要強烈。我覺得在這方面如果能成功的話,就不必固著使用彩色不可了。
問:我特別注意到您所使用的材質。《小棗子》、《七隻瞎老鼠》等都令我格外好奇。因為我看你所用的剪紙,也不是用一般的紙去剪,而是畫過之後再剪。另外還有《沙漠之歌》,可以介紹一下它的材質嗎?
答:《沙漠之歌》用的是剪紙,《七隻瞎老鼠》也是剪紙。但《小棗子》就不是,它用的是油蠟筆。做剪紙創作時,有時用剪刀,有時用刀片刻,和使用畫筆一樣,主要得看使用哪一種工具表現最好。大腦在工作時不要設想太多,因為創作時用右腦,研究時就用左腦。有時候我覺得創作時什麼都可以用,有不滿意的地方,我就會設法做改變,覺得工具不合適,就去尋找其他的工具。所以,創作時不能預先決定非得用什麼材質不可。每一本書都需要經過不斷嘗試,若是太刻板,預先設限過多,往往就學不到什麼東西。你如果做得好,最後的成品會告訴你成功了。
問:《紅獅子》、《狼婆婆》這兩本書都是您自己寫的嗎?
答:我後來的書,自己寫的比較多。自己寫、自己畫,和別人寫、我做插畫有些不同。自己寫、自己畫,衝突的地方比較少,自己跟自己不會打架。如果和別人做,我常常會把自己的想法加諸於作者的創作中,或是乾脆把我的手、筆、和技術讓給文字作者,想像一下,如果他們也能畫,他們會怎麼畫,這是一個挑戰。如果我的表現方式作者和出版社都不滿意,就等於是失敗了。自己寫、自己畫就沒有這方面
的問題了。
問︰在您的作品中有許多表現風格,也看見許多不同的視野和角度,我個人最好奇的則是影子的處理和表現。請問您對影子是否有特別的觀察?或是影子對您來說是否有特別的意義?
答︰這很難說。如果你要表現一個人很悲傷,通常最直覺的就是從那個人的眼睛開始著墨。但是為什麼非用眼睛表現不可?有時候看一個人的背影也會有相同的感覺,這是我從電影中體會和觀察到的間接表現方式,有時候影子真的會帶出許多不同的感覺。至於視野和角度的問題,這也是電影中經常可見的表現手法,每一個角度都會有不同的意義和效果。西畫在照相機發明以後產生不少變化,而畫家們也從攝影中學到不少迥異過往的技巧和表現方式。因此,每次創作的時候,我都會針對故事的內容,以各種角度去表現書中角色的特質和情感。在成書以前都會先畫出許多以不同角度呈現的草圖,在從中選取最適當的表現方式。
問:就畫風而言,小孩對具象、抽象或寫意表現方式的接受度如何?
答︰通常小孩對具象和顯著的圖像接受較快,對抽象圖案的接受度較慢,這是我最近才體會到的事。有小孩以前,我做畫全憑自己的意念,但有了小孩以後,慢慢開始留意這方面的事,也會適度的調整改變。每一種表現方式各有意義,必須針對故事的特性來決定,例如,寫意的手法擅長比現夢境和隱約的幻象。每一個故事都有自己最適合的表現方式。
問:請問您通常創作一本書的時間有多長?
答︰創作一本書的時間沒有一定。我從七歲就開始籌劃「快樂王子」了,從七歲到一九七一年,再到一九七八年,等到出版的時候已經一九八九年了,這大概是我做得最久的一本書。如果創作的過程不需要做太多研究和資料蒐集的工作,時間就會比較短,但是如果需要做許多相關的研究和調查,一時間又找不到資料,就會暫時擱置,時間往往也會拖得較長。
舉例來說,我曾幫Robert Frost的詩集《Birches》(Robert Frost文;1988)繪圖,他是美國非常著名的詩人,我原本對他和他的作品都不熟悉,於是就趁這個機會好好的研究他的詩。讀完後,我覺得他的詩已經很棒了,根本不需要插畫,但是為了幫他的詩配圖,我特別造訪了他的故鄉,看看他成長的環境。我做了許多研究,蒐集相關的資料,用碳筆畫下一張張草圖,有Robert Frost蓋的樹屋、地方上收成季節的景象、雪景、樹林和夜晚的牛,然後再用這些草圖和資料來設計整本書。當然這是很花費時間的。
問:當您缺乏靈感的時候都會做些什麼?
答︰沒有靈感的時候我通常都會做一些和創作有關的研究工作,到處找題材和相關的資料。我無法在一天中安排太多計劃,因為生活中充滿了種種未知和不確定性,有時候會在偶然間發現一些能夠攫住自己注意力,引發興趣的事物,這種事無法計畫。我常常以輕鬆的心情面對一天的生活,看看自己在這一天當中會學到什麼,有哪些收穫。生命中有很多事是偶然發生的,如果你隨時讓自己成為一張白紙,那麼
,各種可能性都會出現;相反的,如果你是一張已經被畫滿的紙,就什麼都不可能了。所以我覺得若是能夠讓自己保持在白紙的狀態,那會是最好的一種境界,因為我永遠無法預期白紙中會被畫上什麼?
問:您在創作時會一次只進行一部作品,還是多部作品同時進行?
答︰同時進行多部作品的時間較多。例如,當我在做《Yeh-Shen》的時候,才簽妥合約就停筆了,停筆時我不能乾坐著等,因為我不知道有關苗族人鞋子的資料何時會出現。如果有別的靈感或工作計畫時,我就會先去進行另一本書,有時第二本觸礁了,第一本卻又可以繼續進行,這很難預料。
問:在您的創作中,自己最喜歡的是哪一部作品?
答︰我最喜歡的書永遠是自己最後一本書,就像在孩子當中最得寵的往往是年紀最小的那一個。小孩年紀大了,離開家以後就是別人的,我有八十幾個小孩,很難照顧得周全,可是它們都不回來看我呢!
問:在您這八十幾個小孩中,有沒有特別難產的?
答︰最難創作的書常常都會讓我留下最深刻的記憶,《快樂王子》就是其中之一。另外《Yen-Shen》也很困難,那是一個關於苗族人的故事,當我創作時發現苗族人並不穿鞋子,而我又不想憑空捏造他們的鞋子,所以簽妥合約以後卻無法提筆做畫。後來偶然在一個圖書館裡發現苗族人在跳舞的時候會穿鞋子,但是要在美國尋找相關的資料也很困難,因此,這本書前後琢磨了很長一段時間,對我的影響也最深。愈難產的小孩對我的影響也愈大,太平常的作品(例如Up A Tree),一、兩月就能畫好的,反而不會為我帶來任何成長。因為在創作的過程中只要遇到問題和困難,我就會特別留心觀察,尋找資料,這對我來說都有相當大的幫助。
問︰現在的兒童出版品非常多樣化,除了書還有影帶、光碟等,不知道您是否想過將自己的創作擴展至其他領域?
答︰我一直在這麼做。每次創作一本書的時候,我都會先看見一部在我腦海中放映的電影,然後再把那些畫面逐一畫下來。這和我喜歡看電影有關,因此在創作時自然就會受到電影的影響。對我來說,做動畫不難,比較麻煩的是必須耗費許多時間畫圖。
我曾做過一本名為《Sadako》的書,描述一個八歲的日本小女孩在原子彈爆炸後罹患癌症的故事。那本書剛開始其實是先做動畫,我先完成動畫,再將它改做成書。那部動畫短片長約二十分鐘,可是為了那二十分鐘的動畫,我必須畫二十本圖畫書以上的插畫,而且為了配合運鏡,還必須把每一張畫都畫得很大,困難度頗高。此外,畫那個故事對我來說也分外辛苦,因為那是一個關於日本小女孩真人真事的故事,所以事前必須做許多相關的研究和調查工作,再加上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我正處身在被日本人佔領的上海,心情非常矛盾。當美國出版商找上我時,我不假思索的一口回絕,我建議他們找日本人來畫,沒有向他們言明真正的原因。但是在我回絕以後,出版社卻仍然陸續寄來許多和這個故事相關的各種文獻資料。
有一回我去加州,準備將這一大堆資料帶去歸還給出版社,結果出版社的編輯要我先聽一卷由一位美國人唸讀這個故事的錄音帶。當我自己在閱讀這個故事時,腦子裡其實沒有什麼具體的畫面,因為這個故事以對話為主,而對話欠缺畫面性,充其量也只能看見兩張交談的臉。可是當我聽完那卷錄音帶以後,畫面突然湧現。接著,出版社的編輯又拿出另一位插畫家畫這個故事的作品給我看,那位插畫家是從大陸逃到美國的中國人,畫風具有十足的紅衛兵理想色彩,我非常吃驚,直覺的認為故事中的小女孩是個有血有肉,確實存在過的人,不能以這種方式表現。所以出版社的編輯要我再試試看,於是,我只好又將那一大堆資料搬回紐約,開始做畫,其間大約經過兩、三年的時間,還去了幾趟日本,實際觀察書中小女孩成長的地方,看看那裡的環境和建築。
自從完成那部動畫以後,我就決定再也不做動畫了,因為實在很辛苦。
問︰國外出版社的編輯對您的創作、分頁和藝術表現各方面,有沒有介入干涉的現象?您認為創作者和編輯之間有沒有一套理想的合作模式?
答︰插畫工作對我來說是一種不斷學習的過程,並非全然以賺錢為目的,每一個故事,我都會盡可能做到自己和出版社都滿意。此外,我和出版社談出版計畫時通常都會先提一個條件,那就是創作的方法必須由我決定。我自己對這樣的工作方式很滿意,因為沒有拘束,這一點非常重要。我覺得創作一本書不是個人的事,而是大家的事,要做到大家都滿意,這本書就會比一個人單打獨鬥做得更好。
輯錄自2001-02-01民生報
|
2020-12-2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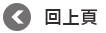 |